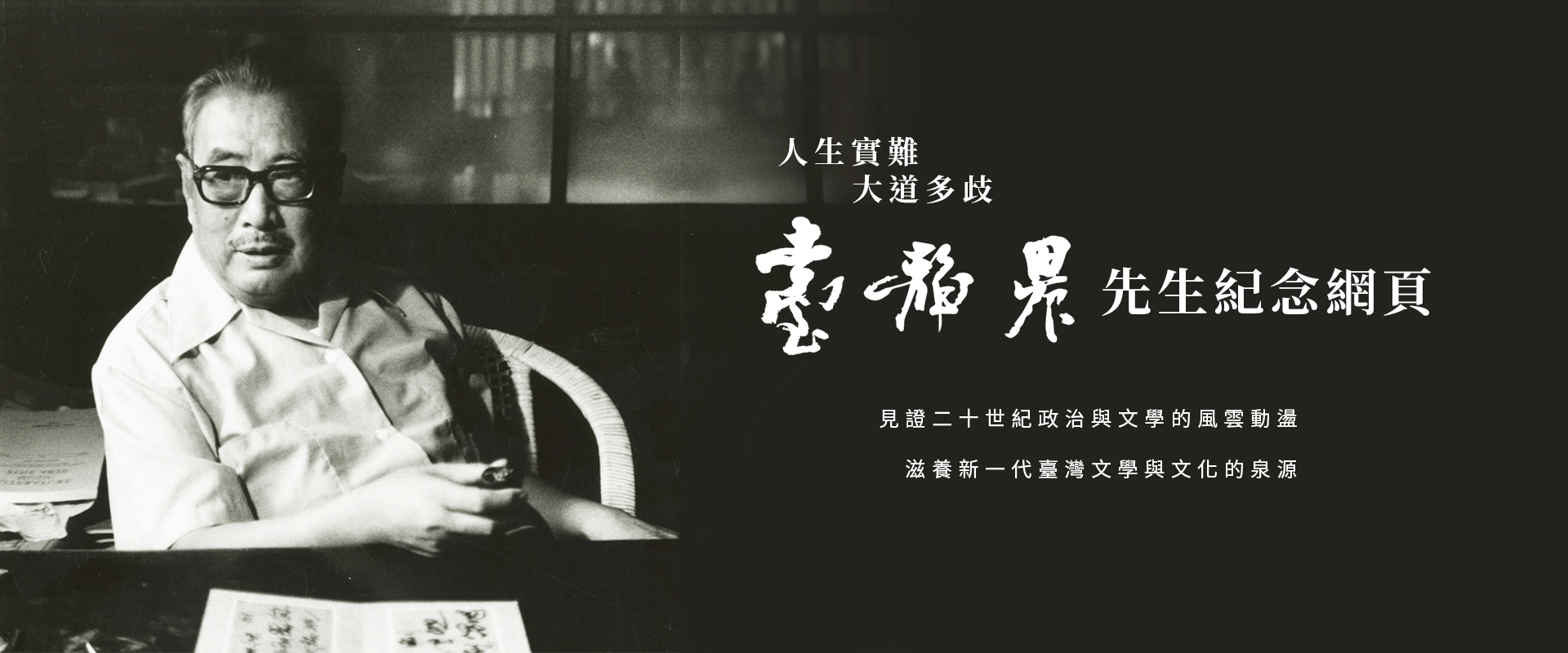一
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,臺靜農出生於安徽省霍丘縣葉家集鎮。他早年接受私塾教育,同時在父親指導下學習書法;進入中學之後,即開始投身於新文藝。時當五四新文化運動方興未艾,中國內外政局持續動盪,青年臺靜農嚮往新時代,滿懷救世熱情與改革理想。一九二一年,他投書《時事新報•文學旬刊》,抨擊繆鳳林等人維護舊詩之形式聲律的論點,參與了當時新舊詩作的文學論戰。初到北京後不久,與汪靜之、胡思永等人共同組織發起文學社團「明天社」,目的正是期待文學界不再幼稚、沉悶,能夠走向「成長的明天,光明的明天,發榮的明天」。
此一時期,他有多篇新文藝作品相繼發表,創作不輟。〈寶刀〉是他的第一首新詩,通篇熱血澎湃,洋溢著欲以寶刀與惡魔戰鬥的豪情:
流盡了少年的熱血,
殲盡了人間的惡魔,
熱血流盡了,
惡魔的種子生長了,
惡魔殲盡了,
血紅的鮮花開放了!
熱血呀,惡魔呀,
不能有一刻不戰爭呵!
臺靜農的少年意氣,由此可見。一九二五年,他初識魯迅,並在其指導下,與李霽野、韋素園等好友共組「未名社」,此後開始頻頻創作短篇小說,佳篇迭出。結集出版的《地之子》寫農民的苦難與困境,《建塔者》寫革命志士的志業與犧牲,皆是體認到民生疾苦,社會黑暗,於是分由「鄉土寫實」與「革命浪漫」兩種不同類型的書寫,投射身為文藝資年的「悲心」與「憤心」。他的小說修辭精鍊,風格沉鬱,深得魯迅賞識,兩人情誼亦師亦友。魯迅編選《中國新文學大系•小說二集》,收錄自己和臺靜農各四篇小說,是當時入選最多的兩位作家。在魯迅看來,「臺靜農是先不想到寫小說,後不願意寫小說的人」,然而一旦動筆,便不落俗套。因此,
要在他的作品裡吸取「偉大的歡欣」,誠然是不容易的,但他卻貢獻了文藝;而在爭寫著戀愛的悲歡,都會的明暗的那時候,能將鄉間的死生,泥土的氣息,移在紙上的,也沒有更多,更勤於這作者的了。
以《地之子》中的〈紅燈〉為例,它敘述鄉間裡一位自兒子三歲起便開始守寡的母親,一心想為搶劫未遂而被處死的獨子超渡。她一貧如洗,連買幾張紙,糊件長衫燒給兒子都無法做到,唯一能做的,是找出兒子年節用剩的一張紅紙,做了一盞小小的紅燈,依照習俗,在中元節當晚悄悄將它放入河中,隨波遠去。兩眼昏花中,這位母親竟彷彿看見她的兒子:
得了超渡,穿了大褂,很美麗的,被紅燈引著,慢慢地隨著紅燈遠了!
這篇小說沒有「偉大的歡欣」,卻正是以悲憫之心,將「鄉間的死生,泥土的氣息,移在紙上」,為悲苦不幸的人生尋找出路。另一篇《建塔者》中的〈井〉,則是層層鋪排出地主與資產階級對於底層農民的迫害,促使敘事者憤然覺醒:
在海南革命的火燄正在光芒四射的時候,中原的革命正在觸機待發的時候,他忠誠地作了一個英勇的戰士。他以骯髒的腳步,邁進新的時代;他以泥土的手,創造全人類的新的生活!
從《地之子》的「悲心」,到《建塔者》的「憤心」,看似頗有轉折,其實未嘗不可視為一體之兩面。而〈井〉或許便可視為綰合兩者的線索:它聚焦於底層農民在地主壓迫下的不幸,父兄被欺壓而相繼亡故的敘事者於是毅然踏上革命抗爭之路,亦是理所當然。
北京時期的臺靜農除了文學寫作之外,先是在北大的研究所國學門旁聽課程,參與歌謠採集運動,收輯整理了大量的淮南民歌,於《歌謠》周刊上發表;兼任北大「風俗研究室」事務員,於民間歌謠、地方風俗方面多所留意。不止於此,他還隨同劉半農、陳垣、沈兼士等師長共同成立「北京文物維護會」,維護北伐後的北京古蹟古物;與莊嚴等好友共組「圓臺印社」,拓搨碑帖,兼治金石印刻。臺靜農日後治學,往往能在一般的文學研究之外,就民俗學、社會學與人類學等面向多所留意,同時兼顧金石之學,應與這些經歷不無關聯。一九三一年,他發表〈中國文學起原之研究〉,從歌唱、樂舞、戰爭、宗教及神話傳說等多方面去論析文學的起原;一九三六年於廈門大學任教時,「見上海《申報》圖畫特刊有所謂『蕃女杵歌』照片」,乃有〈從「杵歌」說到歌謠的起源〉之作,都是此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學術論述。
一九二七年開始,他經由劉復、陳垣兩位師長引介,先後在中法大學、輔仁大學任教。因授課所需,開始思考、檢討中國文學研究方法,撰寫〈中國文學史方法論〉與《中國文學史》初稿;而「中國文學史」也成為他畢生戮力為之的研究課題。一九二八年,臺靜農因未名社出版《文學與革命》而遭到逮捕,入獄五十天後獲釋。此後,他參與左聯,在一九三二年與一九三四年,又兩度被捕入獄,雖然後來皆無罪獲釋,但也因此屢次轉換任教的學校。輔大之後,他歷任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、廈門大學、山東大學教席,幾經輾轉,終因抗戰爆發,舉家遷往四川。
二
一九三八年秋,臺靜農攜同家小,顛沛入川,避難於江津縣白沙鎮,開始川中生活。戰亂之際,如何維持生計,實為一大問題。臺靜農於赴川途中,便先向教育部寫信請求登記戰區專科以上學校教員,入川之後,隨即被分派為教育部青年讀物臨時編輯,並短暫擔任大學先修班教員。他的《亡明講史》,即是為教育部所撰寫的「青年讀物」。一九三九年四月,國立編譯館為逃空襲,由重慶遷到白沙,臺解農受聘為編譯館編輯,自該年九月起任職。一九四二年十一月,他轉任國立女子師範學院中國文學系教授,直到一九四六年渡海來臺,總計在白沙度過八年歲月。
八年的時間雖然並不算長,放在臺靜農的學思歷程中,意義卻十分重大。他偶然結識陳獨秀,兩人時相往還,論學談藝,成為忘年之交。陳獨秀當時抱病撰寫《小學識字教本》,寄寓川中,資料查核不便,多由臺靜農代借閲圖書,親為校訂。再者,在此之前,青年臺靜農致力於新文藝寫作,學術論述,相對有限。然而任職國立編譯館期間,臺靜農負責社會史料整理工作,對於「漢代奴婢制度」與宋代的「文網」、「文禁」事件著力尤深。兩、三年之內,寓目了大量的史料文獻與新出圖書,學術視野,自此陡然開展。他的〈南宋人體犧牲祭〉、〈南宋小報〉等論文皆於此一時期發表,〈兩漢樂舞考〉與〈兩漢書簡史徵〉初稿的寫作,也於此時開始。〈兩漢樂舞考〉博引大量史志與詩賦中的記載,就兩漢各類樂舞的源流、發展進行全面性考述,並指出其中「優戲」與後世戲劇的淵源,自是厚積薄發之作。〈兩漢書簡史徵〉同樣以大量經史類書中的文獻記載為據,考察兩漢簡書的名稱由來、形制、用法,兼及帛書與紙書,為有關「漢簡」的研究發出先聲。只是,此文完稿之後,遲未發表,直到一九八九年才收入《靜農論文集》。據其〈附記〉所言,原因是,
原想看到漢簡實物,與之比證,以致擱置至今,未曾發表。然文獻資料大都盡於斯篇,或尚能供漢簡研究者之參考。
事實上,證諸現今新出土的漢簡實物,臺靜農的研究,幾乎大都與之若合符契。其治學的翔實與嚴謹,由此可見。這一時期所研探的各論題多超溢出一般的文學研究,所以如此,自當與在編譯館的工作有關。
不過,最值得注意的,應是臺靜農文學書寫在這段期間所產生的轉變。臺的創作以新詩為起手式,以短篇寫實小說見重於文壇。實居白沙期間,雖仍不乏小說、劇本之作,但曾經大力抨擊舊體詩的他,此時卻藉由此一詩體去抒情詠懷。這批詩作總名為「白沙草」,詩中多化用楚騷、杜詩詞語,或自抒情志,或感時論事,或寫離散流亡的戰時生活,詩風「鬱怒深沉」,又頗多冷寂森寒之境。臺時居黑石山,山上多梅花,梅花不畏風雪,經霜愈傲,長久以來,便是詩人自喻心志的重要象徵。「白沙草」第一首詩,即是題詠畫梅之作:
皁帽西來鬢有絲,天崩地坼此何時。
為憐冰雪盈懷抱,來寫荒山絕世姿。
它與〈夜起〉(「大圜如夢自沉沉」)、〈孤憤〉(「孤憤如山霜鬢侵」)、〈乙酉歲暮〉(「歷劫灰飛鬢已秋」)等篇什,都以幽冷的意象、繁複的典故,為臺靜農的白沙歲月,投射出身處亂世的感懷與憂憤,並體現回歸古典傳統的書寫轉折。
不止於此,臺靜農還撰寫了不少雜文,由「讀史」出發,博引史料文獻,以「援古證今」的方式評議時事。這一系列雜文以「白沙讀史劄記」為名,廣引野史雜說,頗多感憤激切之言。它始以〈士大夫好為人奴〉,終以〈紀錢牧齋遺事〉。系列文章之中,一再慨嘆的,是「歷史之重演」;念茲在茲並且痛心疾首的,主要是政權動盪之際,飽讀聖賢詩書的知識分子不但缺乏氣節操守,甚至還見風轉舵,醜態畢露。如〈談薙髮〉文末,臺靜農語帶譏諷,以微辭批評今之「猴冠」者忘其祖國;〈紀錢牧齋遺事〉,則以〈附記〉明白表示:
今日的時勢,在任何方面都不能和晚明相比,而比跡於錢牧齋者,卻偏有其人。
另一方面,他的〈關於販賣生口〉與〈關於買賣婦女〉兩篇文章,則是對於歷更上諸多身不由己的流人婦女充滿同情,並且痛加抨擊利用他們「發國難財」的投機分子。所以如此,自是因為眼見烽火遍地,國事蜩螗,避難江津的臺靜農書空咄咄,唯藉「讀史」以自排遣,滿腔的「悲心」與「憤心」,發而為「劄記」之文,亦是不能自已。他之所以寫出〈「謝本師」周作人—老人的胡鬧〉,同樣是職此之故。
檢視臺靜農的文學書寫歷程,「雜文」與「舊體詩」少見於入川之前,之所以頻繁寫作於白沙時期,自當不是偶然。渡海赴臺之後,臺靜農不再寫作新詩與小說,這兩類卻持續不輟,成為他臺灣時期文學書寫的代表。而他的書法由王覺斯而改宗倪元璐,同樣是在這段期間,白沙時期之於臺靜農的轉折性意義,由此可見。
三
一九四六年五月,臺靜農辭去師院教職;十月,應魏建功之邀,赴臺灣大學中文系任教,並於一九四八年起兼任系主任,一九六八年卸任。
舉家赴臺之際,「因沒有商輪,惟搭軍船,行李不能過多」,臺靜農仍然攜帶了大批川中時期抄錄的資料與文稿,作為來臺後繼續從事研究與寫作的參考。來臺之後,臺靜農的工作回歸於以「文學」為本位的教學與研究,然而北京時期的歌謠採輯、民俗關懷與文學研究方法的反思,以及白沙時期的社會史料浸淫,卻是以交融匯通的方式,成為他研究論述與文學書寫的內在肌理。
整體看來,他的學術論文發表多集中於一九五〇年代至八O年代之間,研究論題雖以文學為主,論析之際,卻不僅著重社會風氣、文學預境與文學發展之間的關係,亦多旁通於民俗學與人類學的視角。例如來臺初期的〈屈原〈天問篇〉體製別解〉一文,便是「藉資民俗學的方法,為古詩體的試探」。一九五〇年發表〈兩漢樂舞考〉,為奠基於文獻史料的代表性著作。至於〈魏晉文學思想的述論〉、〈論唐代士風與文學〉 等文,將文學發展與社會現實予以有機結合,亦可視為對於自己早年撰寫〈中國文學史方法論〉的具體實踐。一九八九年,《靜農論文集》出版,彙輯了他渡海前後的重要學術論述,所體現的,即是兼融文史,博雅淵通的治學之道。
文學書寫方面,來臺後的臺靜農不再寫作新詩與小說,改以雜文及舊體詩敘事抒懷。尤其一九八O年代開始,它們與書藝,已成為臺靜農教學生活之外最重要的寄託。他的《龍坡雜文》出版於一九八八年,依其內容性質大致可分為三類:一是閱讀觀覽各類文史篇什與畫作的札記感想;二是自敘、懷人與憶舊之作;三是為各類出版品所作的序文。參照於此前的書寫,不難看出:三類書寫體類上雖沿承早年諸作,風格已有所轉變。尤其第一類因讀書觀畫而發的感懷,實為「白沙讀史箚記」的延擴與轉化:它的所讀所觀,已經不再局限於史料文獻;所思所感,也無關於「歷史之重演」,而是出入於文史藝術之間,終歸於文學本位。渡海前的「悲心」依舊,卻以蘊藉圓融的觀照,轉化了戰時「白沙」陰鬱怨懣的「憤心」。
「懷人憶舊」與「序文」之作,亦各顯精彩。尤其是前者,多為記述交遊,緬懷往事。它銘記了五四以來,一代知識分子與文化人的喪亂意識,以及彼此間詩酒論交,談文論藝的知賞與深情。這些文章多寫於來臺多年之後的一九七、八○年代,當時已是離鄉日久,故舊凋零,臺靜農回望過去,嘆時傷逝,原也是人情之常。不過,這些篇什的意義,其實還並不止於臺靜農的個人回憶而已。經由臺靜農的勾沉點染,它召喚出了一個離亂的時代,那個時代政爭頻仍,風雨如晦,卻仍有一批深具文化關懷與風雅意趣的文人學者,他們各守崗位,或貢獻於學院教育,或致力於藝術文化,在艱難的環境中各懷襟抱,各顯風姿。他們以不同的方式參與了現代中國與戰後臺灣的人文發展,為那個多難的時代,閃爍出動人的光影。
當然,對於其中不少人而言,渡海來臺,或許原本只是離亂時代中的權宜之計,但隨著時光流逝,心境也隨之改變。臺靜農曾撰有不少「序文」與「後記」,分別識記了自己各時期不同著作的著述因由。《龍坡雜文》的序文,正所以清晰地表述出其間轉折:
臺北市龍坡里九鄰的臺大宿舍,我於一九四六年就住進來了。當時我的書齋名之爲歇腳盦,既名歇腳,當然沒有久居之意。身爲北方人,於海上氣候,往往感到不適宜,有時煩躁,不能自已,曾有詩云:「丹心白髮蕭條甚,板屋楹書未是家。」然憂樂歌哭於斯者四十餘年,能說不是家嗎?於是請大千居士爲我寫一「龍坡丈室」小匾掛起來,這是大學宿舍,不能說落戶於此,反正不再歇腳就是了。落戶與歇腳不過是時間的久暫之別,可是人的死生契闊皆寄寓於其間,能說不是大事。
此一轉折,同樣體現於他的舊體詩作。渡海後的「龍坡草」也在歲月推移中,褪去戰時的森冷之氣。這些詩篇或憶舊傷逝,或染閒情,或抒發人生感悟;縱使仍有憂患感時之篇,最終還是多歸於從容閒雅,遠韻綿緲。而最能體現其暮年心境及人生感悟者,莫過於辭世前最後的詩作〈老去〉:
老去空餘渡海心,蹉跎一世更何云。
無窮天地無窮感,坐對斜陽看浮雲。
渡海前的臺靜農痌瘝在抱,感時憂世,然而政治的風雲變幻,時代的波瀾動盪,使他歷經喪亂,壯志難酬。他來臺原本並無久留之意;將住處名為「歇腳盦」,所隱含的,無非是終要回歸故里的想望。在臺時期,他屢發「人生實難」、「大道多歧」之嘆;在最後的詩作裡回首前塵而有蹉跎之慨,原是不難理解。人世的憾悵無窮,一如天地之無窮無盡。但這一切,卻是在「坐對斜陽看浮雲」之中,昇華至另一境界:它既召喚出千百年來,「浮雲遊子意,落日故人情」的同情共感,又以「斜陽」與「浮雲」並置,於天際間交織出美好溫暖的自然圖景。它映照一切人世的聚散離合,悲歡喜怒,也將它們包融進無垠的宇宙時空,歸於永恆。
梅家玲,〈導讀〉(節錄),《史識與詩心:臺靜農績選集》,臺北: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,2024。